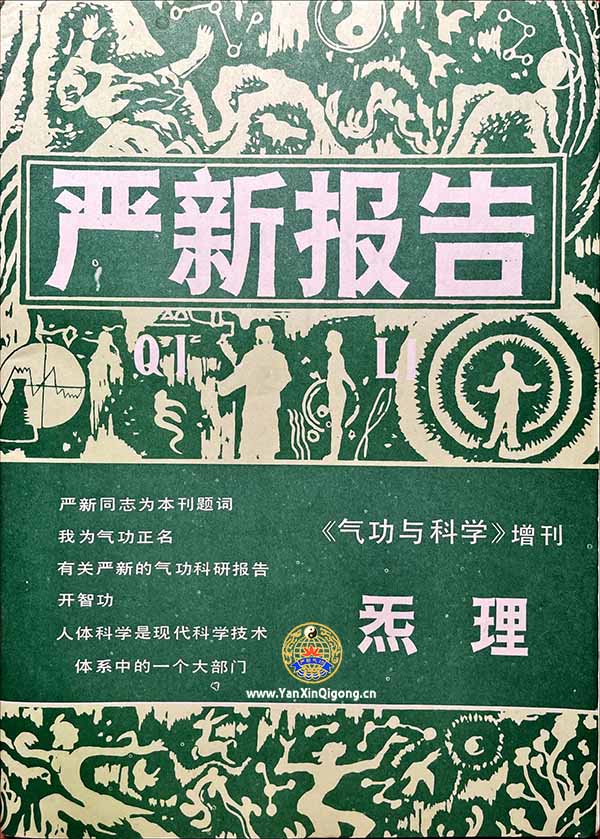严新:我为气功正名(四)
我的气功诊治方法
1985年8月19日,北京拖拉机制造厂一个57岁的师傅宋××,以个人和单位的名义,向我发了邀请,请我为他治病。
当时,我已不在重庆市中医研究所上班,而在全国应邀应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为气功“正名”的事,所以未收到他的信;后来,信七转八转,转到我手上时已相隔九个月。
我在北京,于是通知北京拖拉机制造厂,请他们把病人送到某地点,我给宋师傅治疗。北京拖拉机制造厂的领导很重视,立即派了车和护理人员,把病人送来了。
宋师傅患的是右踝骨骨折,部分组织栓塞,坏死。骨头没接上,已四年一个月了。医院要他做手术,手术后也不能正常走路。于是,他不愿再做手术,寄希望于气功治疗。
他发出书面邀请已9个月,毫无音讯,但他没有怨言。这是很关键的,他相信能找到医生给他治疗。
那天下午我给他治病,方法是让他听讲病例。
治疗时间很短。当时他的右踝骨折处没有复位,又坏死了,脚肿,不能着地,腰酸骨痛,平常坐十分钟也不行,走路要拄双拐加两人挟着,用一只脚走路,一天最多只能走半小时。
我给他讲完病例后,用自来水和开水调和在一个盆里,让他把肿着的右脚洗一下,再泡着。然后我就出去了。
人们都以为我上厕所了。其实我是远距离发功去了。我治病常常是远距离发功的,曾在济南给在北京住院的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发功治病,他和他的妻子,小孩,警卫员都有明显反应。也曾在广州发功,把北京的某些分子结构改变了。
我是下午两时半离开“临时诊所”的,出去时只说出去一会。出去后便上了百货公司,一边办事,一边远距离用功。回到“临时诊所”后,已是下午五时二十五分,就是说,我出去了二小时五十五分钟。
回到“临时诊所”后,在场的许多人脸色十分难看,一见我就转过脸。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们去厕所找不着我,便断定是遇上江湖骗子了。
可病人不是这样想,他的脚一直泡在水里。平常他坐十分钟也不行,这天下午他坐了近三小时仍坚持坐着。他眼睛闭上,迷迷糊糊的象睡觉似的。我拍了他一下,把他叫醒。
我说:“我已经给你治病了。”
他一下子醒过来。在场的人鼻子”哼”的一声, 把脑袋转到一边去了。据说他们已经准备,假如我要收钱,就只给一角钱“挂号费”便算了。他们不知道我给人治病,是从来不收钱的。
在这里,我还要插一句,我给人治病,从不说效果,这是方法问题。如果是有一定把握治疗的病, 我就说没关系。愿意给你治疗的,我就说试一试。治不了的病,我往往说“说不清楚”,如病人非要我治,就说“试试看吧”,或者请病人用多种方法结合治疗试试看。在治疗中,我不用常规的心理疗法,不会问什么“麻不麻?胀不胀”等,从不暗示在治病。为宋师傅治病时,我出去了;或者我在讲课,要求大家认真听,不要想着自己的病;这些都是不想暗示我在为病人治病。
我对宋师傅说:“我治病从不说效果,效果在病人脑袋里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?”
他马上下意识地说:“哎呀,我感到好了。”
我问病人的口头禅是:“你感觉怎么样?”这是客观的问法,好就是好,不需象其他医生问病人:“你好些吗?”有些病人感觉不好,也为照顾医生的面子, 说:“好些,好些。”那些医生是在使用心理疗法。
宋师傅说完“好了”,我就按常用的方法,再给他加一句:“我现在给你收功了。”我收功是没姿式,发功也没姿式,都是用脑发功和收功的。
我说完,他就呼啦啦的把脚从水中抽出来,擦了擦,穿上鞋子一下就站了起来,站起后就开步走。开始的两三步歪歪斜斜的,已四年多没走路,身体不平衡不奇怪。
在场的人足足有20个。他们见宋师傅走路歪歪斜斜,大家“哎哟”一声,都想过去扶他。
我制止他们去扶。宋师傅走了五六步后便正常了,还做了几个下蹲动作。他们的工会主席见了,激动地落了泪。他后悔不已,痛哭流涕地对我说:“严大夫,我刚才差点冤枉你了。我原以为你是个骗子,现在才知道搞错了。”
宋师傅走了几圈以后,我对他说:“你到外面走走,去训练训练,巩固疗效。”我喊了两个年轻人陪同他。我对年轻人说:“你们不要挨着他,可以聊天, 可以照相。”
两个年轻人陪着宋师傅出去,他们为宋师傅拍了些照片,有走路的,有爬梯级的,有跑步的,等等。
二三十分钟后,他们回来了。他们一进门,有人说错了一句活,他说:“宋师傅,快来坐,快来坐,千万不要累着了。”这一说,可完了。所以我得给他加点功夫才能巩固。我说“宋师傅,你还得出外走走,走的时间越长越好,连跑步都行。”
第二次,宋师傅外出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。
这时他已满头大汗了。
在宋师傅出外走动时,我跟在场的人打招呼,说:“宋师傅回来时,谁也不能随便说话,因为我在场时,还有信号,若有人说错话,就夹到我的信号里,就干扰了我的治疗”
宋师傅第二次回来后,我问:“感觉怎么样?”
宋说:“很好。”
我问;“明天敢不敢上班?”
他说“敢。”
他又问:“还有什么注意事项?”
我说:“注意事项就是明天要上班,不上班,信号就退出来,效果就退出来。”
第二天,宋师傅真的上班去了。书记不敢让他上班,要他去拍个片子看看。结果,片子显示:骨折庭愈。
这个病例,否认气功疗效的人是无法解释的。如果要我介绍治疗的方法,就那么简单。
宋师傅这个病起效果的关键,是发出邀请书9个月无回音,他没有一点怨言。我说我出去了,他还把脚踏着水盆里一动不动的,迷迷糊糊的就坐在那里。后来我说已经治疗了,他并不如在场的人那样鼻子“哼”了一声,而是马上下意识地说好了,没有讲半句假话。再后我让他站起走路,他没有害怕,而是慢慢地试着走。要是他不敢果断地站起来走路,那也可能出现麻烦,信号可能马上被退了回来。要他第二天上班,他真的上班了。这几点,宋师傅配合我治病做得非常好。
最近,北京电视台要拍电视,为宋师傅拍了一组镜头,他的情况非常好。
我给病人治病,即使病得很重的病人,只要他能上班,我都是要求他马上上班的。
重庆有个司机叫王运德,因病不能开车,也不敢开车。他说自己患胃病,肝炎等等,已十多年了。他说自己快不行了,已经给爱人留下遗书。
他找我看病。我一看,便对他说:“你主要是心脏有毛病,肝、胃的毛病不大。”
他不相信,并很失望,说:“别人都说你看病很准确,但怎么会诊断我患心脏病呢?我病了十多年, 从来没有医生说过我患心脏病。”
我说:“你不必心急,去做做心电图再说吧。”
他去做心电图,心电图显示心脏严重异常。当时为他做心电图的医生马上叫人扶着他,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,非住院治疗不可。
这一下他真的相信了,并要求我让他住院治疗。
我说:“不行,你找我治病,就不能住院。不但不能住院,还得明天就去上班。”
他瞪着眼睛问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我说:“我就是这么个离奇古怪的医生,找我治病,就要听我的。”
他见我把他的病诊断对了,也服了,忙说:“行, 行,按你说的办。”
我说:“我要求你明天就去上班,答应了,我才开方子。”
他同意了。
我给他开了两个处方共六副药,一天一服,要求他一周以后来复查。
一周以后他来了。我要他再去做心电图,他不同意,说:“人家看过我上周的心电图,说我这个心脏病根本无法治好,最多是控制好转一下。现在才吃药一周,复查不是多余的吗?”
我说:“你这个人老是不听话,不听话就不要找我治病。”
他这才同意了。心电图一做,结果正常了。这下子,他才相信。
王司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听我的话,但他在关键的时候都按我的话去做,他的悟性不低,我一说他就明了,就去做了,所以他的疗效也比较明显。
我给人治病,就是要病人思想觉悟好,悟性好, 要积极配合,与我的思维同步共振。我的师父讲究一辈子吃苦,讲究勤劳勇敢。我也学师父那样。我当医生,给病人看病,如果病人老是想着要休病假,怎能与我的思维波同步共振?怎能配合我?病人一定要想着做点事,疗效才佳。
1986年,我在北京给一个名叫朱桂贞的小学教师治病。她的求治信发出很长时间了。当时我是与国防科委的一个副主任和李常青师傅一块去的。先找到她爱人,再到她家。
朱老师患了严重胸椎病变,还有其他很多病变,卧着不能翻身。我和她聊了几个小时,然后让她睡了几个小时。她醒来后,病就痊愈了。
第二天,她很高兴地送我们走。离别时,我叮嘱她几次:“明天一定要上班。”
她表示:“行!行!行!”
第二天,我到了承德后,发现反应特别强烈。因为我是用强功为朱老师治病的。我使用强功后,如果病人不按我所说的去做,我的反应就很大,难受得很。
我的师傅曾讲过:“不信自然无以明”,这句话意思是说,不信气功的人,不要让他明白,不要让他收效果。你如果硬着头皮给他做好事,就会受惩罚,即有反作用。
当时我的腰椎痛得很。我用功夫查了一下,就对李师傅说:“我们从承德到北京,要路过密云。我们在密云下车,还得到朱老师家去一趟。”
他问:“为什么?”
我说:“我的腰痛得很,朱老师一定没上班。”
李师傅说:”她上班了吧。她有那么好的疗效,怎么不听吩咐呢?”
我说:“不信你去看看,她肯定没有上班。”
我们到车站买票,车票卖完了,只好买了站票,从承德站到密云,站了几个小时,腰部的反应依然不减。
下车时已是半夜三更了,李师傅说到宾馆住,我说不行,我要爬到松树上,腰椎要顶着那个包包上,不顶就不行,非顶几个小时不可。
李师傅不愿扔下我,一个人到宾馆去住,于是整夜在树下守着我。
天快亮的时候,李师傅叫我下来,说老顶着那个地方干什么,不要把肉顶坏了。
我说:“你别管了,你先坐小三轮车到朱老师家, 看她上班没有。”
李师傅赶紧找个车子去了,不久来说她果然没上班。
她在家干什么呢?私心杂念太重了,怕上班后请假不容易,上了班又要做事,要劳累。看到自己病后好长时间没人做家务事,于是打算用两天时间 洗五床被面和全家人的几大盆衣服。她以前洗衣服用凉水洗会过敏,都是用热水洗。她听说我给她全身治疗,见好了,可沾凉水,所以高兴极了,想把家来个焕然一新,准备第三天才上班。
李师傅回来后,跟着我就去了。我当面把她批评了一顿:“你干什么不上班?你看麻烦了……”
她知道不听叮嘱,做错了,赶紧上班去了。上班后,疾病没有复发,身体一直正常,最近电视台 还拍了她几组镜头。
她上班后,我的反应消失了,腰椎疼痛也好了。
有些悟性差的人,不懂配合我治病。对这些人,在诊病时,我往往把他说一阵,甚至把他说得很不行。
为什么?他违反了我治病的规律,信号加不进去,不说不行。
1985年春节回家,有个鼻咽癌患者找到我家求治。见着我,就哇啦哇啦地把病告诉我。
我对他说:“这病没关系,你不要焦急嘛。”
但他不领情我的意思,还是非要把病情讲清楚不可。
我诊病,一般不让病人把病情说清楚,所以马上制止他说话,叫他把病历拿过来,假装看了。
这几年,因为找我看病的人多,一般我是不看病历的,这次不得不假装看,还假装为他把了脉。
我对他说:“没多大问题。”接着,我告诉他回家后怎么怎么办。
可他就是悟性差,非要把病情说清楚不可。我便打断他的话,说:“我已经给你把过脉,看过病历,这就行了。你按我的方法做就行了。不要再说了。”
结果,把他弄得很不高兴,马上离开我家,一路上怒气冲冲的。
1987年春节,他又来我家,说要当面感谢我。说他那次看病后,按我的方法去做,过了一段时间去检查,癌症没有了。还问怎么解释。
当时我不在家,我父亲对他解释说:“他(指我) 就是这样的,他把你骂一通,就是免得让你想着那个病,你就想着这个医生太可恶了,想着想着就把自己的病忘掉了。”
父亲的解释是有道理的。我平常从不愿病人感谢。
上述的治病方法,是我常用的方法之一。
有些悟性差的病人,老错过机会,加了几次信号还不行,只好第二次去治。
重庆空压厂工人蒋志黎,30来岁,骑摩托车被东风牌汽车压了,致胸11椎骨折,胸12椎严重变形,高位性截瘫。
蒋受伤后,有关医院为他照了片,专家医生会诊后,说他伤得很严重,以后能坐轮椅就不错了。医院说没有病床,不接收他。所以他在家躺着,天天“哎呀,哎呀”的叫个不停,不停地服用止痛药。
他受伤后的第三天晚上,肇事司机的单位及病者单位的领导找到我,把我带到他家。
我治病是用聊天的办法,看病人怎样答话,如果他有悟性,懂得配合我,我一加信号就进去了,否则,信号很难加进去。
我问蒋的母亲:“你的孩子是在医院治疗好还是在家治疗好?在家治疗可能时间会短些。”
他妈妈说:“如果你们研究所有病床,当然是在医院治疗好。在家里我们不好照顾。”
其实,这家人家知道我曾给附近一个类似的病例治过病。那个病人是从高楼摔下来骨折,只消一刻钟就被我治好了。这附近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,所以这家人才会找我给蒋志黎治病。蒋的母亲答话答得不对劲。
我又问蒋,他悟性也很差,说的和他母亲一样。所以,这一次就没法治疗。
我对肇事者单位和病者单位的领导说:“你们把我找来干什么?听听病人及家属的意见吧,人家情愿住医院治疗嘛。你们要考虑病人的情绪,还是再与重庆的大医院联系好了。如果实在没有病床,在家住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说完,我向门外走去。脚跨出门口时,我又说:“你们配合得一点都不好。要是配合得好,马上就可以起来走路。”
我走后,他们互相埋怨。一周后,他们两个单位的领导和医生又来找我。
我对他们说:“现在病者还有顾虑,不好治。”
他们说:“没有顾虑了。”
我说:“他还有一点顾虑,他担心他的摩托车烂了要花一笔钱维修,还担心养伤没有营养费。”
他们领导说:“没关系,他要多少,我们给多少。”
我这才同意去。
到了病者家,病者一家人都说想通了,不想找医院治疗,就找我治疗。”
我说:“你们想通了就好办了,但蒋师傅还有点没有想通。”
蒋马上说:“通了通了。”
我说:“你还想着要营养补助。”
他笑着说:“哎呀,这个不好意思说,确是还想着这么一点儿。”
两个单位的领导马上表态:“随便你要多少。”
蒋说:“我本来不想说,但严医生都说了,我不要多,只要三百元营养费就行了。摩托车压坏了,还要修修,大概要几百块钱。”
蒋师傅的表态很关键,他说了真话,而且要求不高。所以,领导一听就非常高兴,说:“你这三百块钱营养费太少了。我们邀请严大夫时已经说过,如果他能在半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把你治至能坐轮椅,我们就奖给他3至5万元。”
我告诉在场的人:“你们都出去,可以在窗外观看治疗。我也出去,在远处发功治疗。”
大家都照我的话去做。不到一刻钟,病人开始活动,不到半小时,病人就下床了。我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,但可与病人的房间互相通话。
病人起床后问我:“严医生,我的鞋子在床下怎么办?”
我说:“你还要我给你拿鞋吗?你自己去拿!”
于是,他趴下床,把鞋子取了出来穿上,高兴得不行,跳呀跳呀。他开了门,外面的人进来了。
我问:“行不行?”
病人说:“行!”
一个截瘫的病人就这样治好了。我实际用功只半小时。
1987年在北京,我遇到一个病人,姓尹。他手臂粉碎性骨折,医院为他复位后,骨头卡住了韧带。
医院说要动手术但没有绝对的把握,手术后仍难免有残废的可能。
当时,我的住所有许多人,有安全部的领导和新华社记者。病人不敢进门。
我说:“小尹,你进来呀。”
他手里打着石膏,进来了。
我明知故问:“你手上绑的是什么东西?”
他说:“石膏。”
我又问:“石膏起什么作用呢?”
他一听十分敏感。大概他事先知道我治病的方法,马上说:“不要了,不要了”。就在椅子上解下绷带拿下石膏。在场的人都制止他,我打手势要大家不必制止他。
我对小尹说:“活动活动,看还痛不痛了?”
他动了动,说:“不痛了,不痛了。怎么刚才还在痛,现在就不痛了?”
我没有直接回容,而是再问:“敢不敢做俯卧撑?” 他说:“敢!”说完趴下就做起来。
平常他只能做4个俯卧撑,他做了4个以后便问 我:“严医生,您说还做不做?”
我说:“还能做吗?你看做不做?”
他说:“能做!”接着又一连做了10个。起来后,我说:“就这样吧,明天上班去。”新华社记者一直看着,还想在我治病时拍些照片,可是这短暂的时间一下子过去了,他根本没想到治疗过程会这么快。他很后悔错失了这次拍照的机会。
还有一件事。辽宁省某厅长的爱人,姓杨,她膝关节有两颗很长的骨刺,连外行人看她在医院拍的照片都看得清楚。她的腿不能弯曲,走路困难,要慢慢抬起腿走路,上下楼梯更是困难。
那天,厅长带他爱人来,但没有让她进屋,自己先征求我的意见,看是否能够安排。他是事先写好一个字条准备递给我看的。他进门,还没有递字条,我就开口问他:“你是不是要带爱人来治病?”
他很吃惊,说:“对了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 我说:“我是猜的,我就是爱猜。你快叫你的爱人进来吧,不要把她丢在车上。”
于是,他去把妻子扶了进来。
我对他的爱人说:“杨老师,我治病怪得很,你要听指挥才好,敢不敢?”
她说:“敢。”
我说:“听指挥,出去跑步!”
她说:“行!”拔腿就跑,跑了20分钟,腿也发热了,回来时挺高兴的。
厅长对她说:“来坐坐,看严医生要不要开点药。”这话说错了。已经完全好了,还需吃什么药?他这样一问,意思是病还未全好。这就干扰了我的信号。
我说:“你还得再出外跑一回。”
她又跑了一会回来。厅长不敢说话了。就这样,她的骨刺便消失了,膝关节正常了。
辽宁省一个领导同志的爱人,因腰椎骨结核导致一条腿走路麻痛。平常最多只能走两三百米远。 她听说某厅长的爱人能走路了,她也很感兴趣。于是,这位领导同志带她和新华社记者找我。新华社记者是一直跟踪采访我的。
省领导同志的爱人姓张,她见到我后,立即讲病情。我说:“不用讲病情了,新华社记者早一步用信介绍了。”实际上,我是制止病人讲病情。
接着,我就与他们聊天。先说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的故事。我讲别人的故事,实际是对病人讲。我们聊到半夜,我便对她说:“张老师,你胆子大吗? 现在敢不敢出去走路?时间越长越好。”
张老师平时穿平底鞋走不到二三百公尺就要蹲下,这时她穿着高跟鞋,能走吗?所以当时那位领导同志一下瞪大疑惑的眼睛,想问我。我打手势不让他问。
待张老师走后,我才说:“你不要害怕,没有把握,我怎么敢让一个女同志三更半夜到外面走呢?”
四十八分钟后,张老师跑回来了。她说一气走了几里路,越走越轻快,特别是有病的那条腿特别有劲。
那位领导同志听了不大相信,说:“你的感觉是不是真的?”他怕我事先与她商量好,或是新华社记者事先与她商量好,好让自己表态支持气功。
其实,我与他爱人从不认识。当然,那位领导同志不相信病好得这么快,这也不奇怪。
他又问妻子:“你真的越跑越轻松?”
她答:“怎么不是真的?”
我见那位领导同志不信,又叫她到外面跑一会。
二十分钟后,她兴奋地跑回来说:“好了,好了,没事了,这回真的好了。”
于是,我准备收功了。
可是,那位领导同志还不放心,让我帮她开个药方。这又搞麻烦了。后来我想,省领导同志明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,总不能让他等一通宵吧,只好开了个方子。这个方子实际是应付的,吃与不吃差不多,不起多大作用。反正,病人的大问题解决了,但小毛病还留一点儿。
最近,她又跑来找我。我问她感觉怎么样,她说没事了。现在能走路,可以连续走好几站路。她不坐汽车上下班,都是为了锻炼。当然,偶然天气变化,患部还有点不舒服。大概就留了这么一点。
有一个女同志,是国防大学一个干部的爱人。 她有只耳朵患有老年性耳聋;还有小脑控制失调症,走路朝一边倒。医院采用高氧舱等办法,仍治不好。
1986年9月的一天晚上九时左右,她被人扶着来找我。当时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带她来的,他想让我做实验,好让其他教授相信气功。
实验时,教授用棉球把病者听力好的耳朵塞住,然后让病者用病耳听手表的走动声。我发功了一会,病者失聪的耳朵可以听到手表的走动声了。
我对病者说:“找我治病的人一定要胆量大,你行吗?”
她答:“行!”
我说:“你现在一个人出去走路。”
当时我的住处在郊区地带,相距很远才有一盏路灯。我对扶她来的人说;“你们不能扶她。”
她说:“行,我自己去走。”她走起路来,不再往一边倒了。
她按我的荽求,出外走了四十分钟按时回来。回来时高兴得很,还未进屋,就开始嚷嚷闹闹的,说;“哎呀,这下子我完全好了,小鸟的声音我听着了,别人洗衣服的声音我听着了,走路的脚步声和远处的汽车声都听着了。”
她进屋后,我让她坐着。因为我要问话,才能收功。
我说:“黄老师,你感觉怎么样?”
她是在某研究所当秘书的,说话习惯婉转,她答道:“好一些,好一些。”
完了,这就只能“好一些”了。此时,我又不能直接说她讲错话,只好对她说:“你的悟性太差了。”又叫她出外再走半个小时。
她走了三十二分钟,回来了。这一次,我不能直接与她对话,便跑到隔壁房间去。在这之前,我与在场的人打了招呼,叫他们先批评她,但又不要直接批评,要旁敲侧击地批评,要跟她说清楚,说话要实事求是,不要留有余地,但不要直接说她刚才说错话。
过了一会儿,我从房间出来,不再用以前的方法了。我问:“黄老师,你好久没上班了吧?”
“是,两年半了。”
“你是否想上班?”
“想上呀!”
“假如病好了,你敢不敢上班?”
“敢! ”
就这样,间接表态,就成功了。
所以为人治病,有时要病人答一句话很麻烦, 表态错了,要浪费很多时间。有时晚上跟病人聊天治病,要谈很长时间,主要是病人不懂得配合,有时讲大课,也要延长时间,也因为听众不懂得配合;有些人,本来有好的感觉,但又怀疑,又否认,这就不好办了。
国防科工委有个医生,是我国最早的首长保健医生之一,曾当过高级首长保健医生。1986年我被邀请到国防科工委搞科研时,他是我的指导,我与他协作开展科研工作。他夫妻俩都是西医生。
一天,他爱人的血压突然升高,收缩压从120 升到178,舒张压从80升到98。头剧痛。医生不敢轻易用药物,只是慢慢地观察。
那天下午,他与女儿一起来找我。他女儿是研究生。他说:“严医生,你得为我想个办法治治。”
我在水龙头盛了一杯凉水,然后叫他女儿把手表取下来。我要通过他女儿为母亲治病。这手表是一圈金属,干扰了她的磁场。
取下手表后,我通过手表观察一下信号,因为手表有他女儿的信号,也有他爱人的信号。手表还反光,上面能看到他爱人的图象。
我对他女儿说:“小玉,你敢把这杯凉水喝下吗?”
小玉说:“敢喝。”咕噜咕噜一下把水喝下肚去。这水通过女儿向母亲传递信息。
我说:“小玉,你赶快跟爸爸回去看看你妈妈,量一量血压,然后来一个电话。”
他们的住处与我的住处相距一百多米,来去不过一刻钟。他们回去后马上量血压,然后来了电话:“血压从178降至120,低压从98降回80。头不痛了。”
因为病者没有吃过降压药,就只有她女儿喝过一杯凉水这么一个过程,在人们看来,不是稀奇古怪吗?
说到小玉,还有一段插曲。
她原来脊柱弯曲,考研究生,人家不愿收。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,人家才勉强收了。
有一次我到他们家里。玉的父母对我说:“严大夫,你看看我小玉的脊柱。”小玉的父亲知道我的治病方法:看病不许说病。
我说;“脊柱没问题呀,是正常的嘛。”
小玉的母亲马上说:“哎呀,她有……”
话还没有说完,小玉的父亲就一下子把她的话打断:“不要作声,你进屋快看看小玉的脊柱,肯定好了。”因为他知道我的方法,观察过一些病例。
小玉的母亲马上去看小玉的脊柱,真的端正了。 从此,小玉对我的医术非常信服。
糖尿病人是不能多吃糖的。有时我给糖尿病人治病,非要他吃糖不可。
北京拖拉机公司有一个检验师姓刘,患有糖尿病,找我治疗。
我对他说:“你这么一点儿病住院干什么?”
他不表态。不表态,信号加不进去,浪费了。
我又换一个方法,叫他回去喝加糖的三磅装牛奶6瓶。
他听了,把眼睛瞪得很大的。检验师自然知道糖尿病人要限制饮食,特别限制食糖,我要他喝加糖的牛奶,不是开玩笑吗?他又不表态。
我说:“你不表态,加喝6瓶牛奶,连喝一周。
他爱人马上拉他的衣服说:“你还不表态?”
他这才哆哆嗦嗦地说:“行,行,行。”
当晚他回到北京一家医院后,趁医生护士不在,同房病友都睡后,偷偷地把爱人送来的6瓶加糖牛奶喝了。在喝牛奶之前,他曾做过检验,尿糖为三个“+”,阳性。喝完牛奶的翌日,再作检验,尿糖一个“+”号都没有了,完全正常了。
不仅他正常,同房七个病友,有两个也正常了。另外四人从四个“+”号变为一个或二个“+”号, 都有了明显的好转。观察一周后,他要求出院,但医生还是没让他出院。以后又观察了一年。
不久前他见到我,说病愈以后没有反复,还参加了游长城活动。
他的血色素原来也很低,现在达16克多。医生对他的病愈表示不理解。
与我共做科研实验的教授中,有个陆教授,原是清华大学的,现到了中国科学院。在做一系列科研实验之前,我是为他治过病的。
有一天,他突然脑血管意外,人都昏迷了,如不及时抢救,人就会死去。即使救过来,也有后遗症。’
他爱人立即打电话来告急。我对他爱人说:”你把电话筒放到他的耳边,让他听我说话。”实际上我是通过电话筒给他治疗。
过了三分钟,他能说话了。再过一刻钟,他能站起来走路了。
陆教授在电话问我:“严医生,明天我能上班吗?”
我说:“照常上班。”
这次,如果还说不上是救了他的命,至少也可以说是把他严重的脑血管意外纠正过来了。他没有后遗症。
陆教授的儿子在美国读书,患有严重胃溃疡及其它一些病。一般的留学生,在美国除了读书外,还要找工作做。这种类似“勤工俭学”的生活把人搞得很紧张。如果身体有病,就麻烦了。
陆教授问我能否为他儿子治病,我说试试吧。我给他一个条子,叫他给儿子寄去,并带上一句话:晚上最迟什么时间进房间,按美国时间算。就这么一句话,气功的信息就会带到美国,就有可能为他儿子治病。
陆教授真的照办。
后来陆教授来信来电话,说他儿子的胃真的不痛了,这件事离现在已一年多。
前不久,陆教授的儿子回到北京。当时我在沈阳。他打电话告诉我说:“严叔叔,我收到你的信后,到现在已经一年多,胃都不疼了,饭量增多了,身体好转了,成绩也上去了。”
这病例说明,气功信息可以为距离很远很远的病人治病。
我曾与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在一起做实验。
有一天,在总参某部一个政委家里做了一次实验。当时包括其它教授共有6个人,其中有个是年轻人。
清华大学一个副教授姓朱,他患有水肿病,用手指一按小腿,就会凹下去一个洞。他让我为他看病。我说,不用管它,大家聊天吹牛皮吧。
聊天吹牛皮,实际是我治病的方法。我讲起济公的故事来。那个年轻人陆陆续续上了5、6次厕所。他红着脸对我说“严大夫,请你帮我看看我的内脏哪里出了毛病?今天我真不好意思,上了5、6 次厕所,过去我的肾脏从未出过毛病。”
我笑了笑,对朱副教授说:“朱老师,你卷起裤脚按一按小腿看看。”
朱副教授真的按了按小腿,高兴地大叫:“哎呀,真神,我的腿不肿了。”
我说:“你腿上的水都跑到年轻人身上了。”
人吸收水分,不一定要通过口腔,还可从别的途径。南方空气湿度大,人不觉口干,皮肤不干燥。北方则相反。如果人身上的水分蒸发快些,那么,让吸收快些不就行了吗!
1987年1月24日、9月24日的《光明日报》、 《人民日报》等报纸曾向国内外报道过我与清华大学做实验的情况。有一项实验是用气功改变液体的分子结构,包括改变水的分子结构。
科学界有人认为,世界上最简单的分子结构最不容易改变。水的分子结构就是如此,很稳定,你把它加温成开水,降温成冰块,水的分子结构都不改变。人体内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水,如果能把人体的水分子结构改变了,就可治疗某些病。刚才的例子就是改变了人体的某些分子结构,使水分从一个人身上跑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了。这不是迷信,“法眼通”就有这种“纠正”的功能。
1987年春节过后,我本想在四川逗留一段时间。因为海灯法师要我到成都看看四川原省委书记杨超同志。
结果还未到成都,北京方面有关负责同志,通过四川省公安厅,绵阳市公安局,派人找到我家来了,说北京有重要任务,要我马上就出发。
到了北京,我才知道要给一位重病同志治病。
这个同志患了肝癌,到了晚期,转移到很多地方。曾告病危两次。在某医院住院。
我进医院见他。他开口就说:“严医生,你只给我治三次好了。”他看过有关报刊对我治病的报道,说得很认真。
这人真怪,只要治三次。但这句话起作用了。 我去了一、二次,病者病情好转。原大便出血,消化道带血,大便潜血阳性转成阴性了,高烧退了、黄疸减退,剧痛消失了,原来用“杜冷丁”,后来不用了,肝脏敲打也不痛,能下床活动,洗澡,吃稀饭。
可是症状改善后,他思想并没有纠正。他爱人和医生曾骗他不是癌症,说是其它病。但他偷看了病历,知道是肝癌晚期,于是他写好了遗书藏在抽屉里了。
他对爱人说“没关系,没关系”,但心中就是不想活。他只想找个医生止痛,不痛了,他就要下决心去死。
因为病者只要我治三次,这话是起作用的,所以第三次我就不去了。他的领导及有关医务人员包括郭沫若的女儿也来给我做工作,说病人家属和医院希望我给他再当面治疗。大家也想见见我。
我说我不能去第三次。但有些话又不能讲,想纠正又纠正不了。
过了二周多,家属、领导、医院都来催,说病者要求最后与我见一面。
我一听,最后见一面再不去,可要欠他一笔帐了,只好当天晚上去了。
这病例中间出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,真令人不可相信。
我治病练功期间,都是自己住一房间的。就在我第三次去医院之前三天,我的房间出现大血臭。新华社记者与我爱人住隔壁的房间。那天早上,我马上把新华社记者和我爱人叫来了,她们进房后也嗅到血臭,这就意味着那个病人要大出血死亡。
我告诉他们:“不好了,病人很可能要死于大出血,但时间不好说。”
过了三天,即我去的那天,病人突然大出鼻血不止。信号过来后,我用功把它止住了。
晚上,我到医院后,我爱人说她不舒服,便留在楼下的车上。结果我一上楼到病房,她就呕吐了,闻到很大的血臭恶心,她也出鼻血了,紧张得很。病人则精神很好,非常高兴,说了很多感激的话。
我们聊天虽然投机,但他思想很顽固,想着身体不行了,不如早点离开人世。这个决心下得太大了,不好纠正。因为气功治病总得两相情愿。
我暗示他:“你的小孩多大了?”
他说:“9岁了。”
我说:“明天你叫人把他带来,看看他有没有特异功能,我给他激发激发,以后你再培养培养他,对国家也有贡献嘛。”
他摇摇头说:“没有必要。”显然他对“明天”都不感兴趣。
我又换了第二个角度暗示他:“你爱人小陈年纪轻轻在法国留学,你病好后要指导她学外语啊。”
他又摇摇头:“她有她的出路。”又摆手拒绝了。
我又从第三个角度暗示他:“你的领导对你很关心,前两天专程来叫我尽快治好你的病,说有重要任务,听说你还是接班人,他对你非常重视的。”
他又“唉!”了一声,接着说:“没意思,没意思。”一而再,再而三地,他的兴趣就是激发不起来。
最后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了,用四川土话讲是“月亮把里耍关刀——明砍” 了。
我用激将法,突然大声对他说:“你怎么搞的?”他吓得瞪大眼睛。
“你想着跳楼干什么?这个想法可又错了!” 他听了死死盯着床。
我还以为他会说:“唉,没有,哪儿有这个想法哟!”但他根本不表态,两眼死盯着床,这不是默认了吗?
接着,我象交朋友似地啰啰嗦嗦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会儿。他只是很有礼貌地听,很少说话。
后来,他下地来活动活动,然后对我说:“严医生,我洗澡行不行啊?”
我说:“行啊。”
从晚上8点开始聊天聊到11点,我就出来对他爱人说:“小陈,你今晚可要告诉特护(特殊护理,24小时都守着病人),今天晚上一定不能睡着了,要随时观察他的吸呼、心跳、血压、脉搏及其他情况,有情况及时报告值班医生或打电话给我。”
他爱人不在意,说:“这几天他精神很好,一天比一天好,就能活动了。”
我说:“你别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啊”
她说;“行行行。” “行”到1点40分,她睡着了。 护士在2点40分左右去打开水,把她敲醒,她“唔唔” 应了,又睡着了。护士打开水回来,见床上没人,卫生间没人,窗子打开了。不好办了,14楼,哪还有人呢?当然没人了。
这件事已经公开了,我才讲。开追悼会时,他爱人才大声痛哭,什么事都倒出来了。她哭喊着:“对不起呀,严医生已告诉我你跳楼的想法是错的,后来又告诉我不要睡着了,可我就是睡着了……”
这事后来人们都知道了。所以病人不配合就难办,气功师傅就对此深有同感。我在沈阳讲过这点,那些懂气功的道长、法师都翘起大拇指说:“严医生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了。”
用功夫为人治病可不是那么简单、舒服的事,就如我那天晚上告诉病人不要跳楼,他不表态那样, 当时我的大牙当即咬下来,咬成两半,后来到北京一个口腔医院,技术最好的院长给我包的,他问我,要不要把牙拔了,我说我是练功的,拔了要受影响,就包着。包了现在有时也受点影响,这就是损害。
还有那天晚上从医院回到住处,第二天一早,我起来后头特别痛,一摸,头上有一个坑,大指头都可以放下。我叫了起来:“哎呀!这个人麻烦了,麻烦了,他不表态,你看,麻烦了!”
新华社记者在隔壁跑过来问:“什么麻烦了?”
我说:“你一会儿就知道。”
一会儿就有人报告说那个病人大出血,晚上死亡了。当时他没说具体情况,我也不想说,说了对医院也不好。我只说:”怪不得我头上有一个坑哩。”
新华社记者为了证实一下,问:“能不能摸一下?”
我说:“可以。”他们几个人就来摸,果真有一个坑,几天后才恢复。
后来病者的领导听新华社记者说我头上有一个坑后,来问我是否真实,我说是真的。他一下竖起大指头说:“现在我相信气功了,可理解气功是怎么回事了。”后来,他又悄悄告诉我:“那个病人头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这样的坑,我请了个整容师从早上7点干到下午4点才给他修好了。”
安全部那位肝癌患者留医的医院院长,不相信气功,非要我做气功实验不可。
我说:“好吧,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:’疼痛传染’。”
疼痛怎会传染?医院的院长、医生、护士都不信,结果,凡进安全部那位肝癌患者房间的人肝脏都痛,邻近病房的病人肝脏也痛,有些人的家属也痛,一下子“传染”了几十人。搞得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紧张了。他们经过亲身体验,也都信了。
这是什么道理?用气功的话来说,就是气功师把病人的疼痛转移出去了。医院的院长说要做实验,我就把这些“疼痛”转移到患者周围的人身上。当然,其它人肝脏有痛感,并不是染上肝病。有人进医院检查了几次,肝功能都正常。
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有时气功师把病人有毒的气排到附近的大树上,树身顿时生出个包包来。
有些人不理解气功,他们不懂得配合,又总想有好的效果,这样,气功师耗损能量很大。
有时,对某些特殊的病人,为了取得好的效果,气功师是用强功进行治疗的,一次下来就损耗很大。 如前面所说头上出了个坑,就是用强功后,病人不愿配合,把信号反射了回来造成的。这个坑,过后要练功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
去年我为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治病,我体重下降了20多斤,那一个多月几乎吃不下饭。“两弹元勋”的五大危机症状在治疗第3次以后就改善了,能起床了,还可以在医院考虑工作了,饭量一天比一天增加。原来癌症全身转移,全血象下降。过了10天后,全血象回升,其中几项指标正常,只有血小板还不正常,但也回升了三倍。
本来,首长指示是要我为抢救邓稼先尽力的。可是,在病情好转后,我的措施老不给我兑现,我虽然努力用功,效果也不会很大的。这样,干扰实在太大了,我只好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”,上五台山找师傅去。
本来我是为了给气功“正名”的,但当时不走,既无法兑现我的治疗方案,又会为气功抹黑。所以我不得不走。其中的苦衷,内情人才理解。
有人说:“你常给那些重要人物治病,不怕出麻烦吗?”
我说:“若要出麻烦,我自己就得来个’金蝉脱壳’,先打招呼,若不听,也不一定非要’和氏献璧”, 非要断腿才行啊。现在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,大家不行,我也不行,气功也不是万能的。”
有些人不理解气功,到病危了才来找,找着了还要埋怨,那怎么行?我干脆得很,不配合,把我闲着,我就走,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”,不是非要病人死在我的手中。
气功师给领导干部治病,往往领导干部本人配合,但他周围的人不配合,如家属、保健医生等等。干扰就从这些地方来。
我听一些气功师说,他们给一些首长治病,首长的保健医生说:“你看,气功师就是为了争政治资本”其实人家用了功,为首长治病,怎么是捞政治资本呢?这种说法就不好。
我最近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,一用功,头发白了许多,我原来没有白头发,为什么一接受这一任务,头发会白了许多?电趣台的同志也问我的头发是怎么搞的,20来天就白了。我说这一特殊任务不加功不行,加功了也不行。加功,还要考虑左邻右舍的人来干扰。包括现在,我还在远距离用功哩!
我讲这些例子是希望大家要注意气功这一特殊手段。要想收到较好的疗效,就要尽量去配合气功师。
在重庆,我爱人一个同学丢了一张空白支票,上面印鉴齐全,只要填上数额就可购买物品。
支票丢失后,她赶紧到报社,当时是元旦期间,报社说,版面已经排满,无法登遗失声明。她又找电台,电台也说节目安排好了,不能插内容。她又到银行,银行说,现在是节日,不挂失。
这下可完了。这张支票可以在重庆任何一个百货公司购物,可以买上几万元物品。
我爱人的同学很焦急,她知道我有些本事,曾用气功破过案子,于是连夜与爱人一同找上门来。
为了使他们相信气功,以便配合我,我带他们一起去找我的学生,一个8岁的女娃娃。这个女娃娃在我给她治病时,发现她有遥视功能,所以我把她收作学生,加以培养。
到了女娃娃家,我把她的父母叫醒,叫他们把女娃娃叫醒。但不要开灯。我对女娃娃说:“你照我以前教你的方法看,看到什么说什么。”
她看了一会,说:“哎呀,严叔叔,我看到一个娘娘(重庆人对阿姨的称谓)在厕所里从兜内拿出四张票子,是用回形针别着的。”接着把厕所形状描述了出来。
她这么一说,站在屋外丢支票的女同志马上回忆起来:“是四张支票,用回形针别的,是在厕所里取过的。”
我叫小女孩继续看。
她看了一会,说:“娘娘拿出四张票子后又放回兜里了,后来又上了汽车。上车后,一个穿皮茄克的小伙子从她兜里拿走了。”
我问年轻人哪里去了。
她说:“下车了, ”并把图象勾划出来,“下车后,到了江边,我看不见了。”
到了江边,小孩的功能就不行了。因为她怕水。 这下子,那对夫妇对气功,对特异功能相信了。
我说:“一周内,我给你们查出来,不过你们要配合好。”
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是不整人,即使过去我帮公安局破案,破了也想法让犯罪分子立功赎罪,给他出路,所以被我破了案的那些小偷都跟我关系非常好,他们以后也不偷了。
我对那夫妻俩说:“现在你要解决这个大问题,需要丢点小钱。”
她不表态,这就麻烦了。
我说:“你们家里的存款、存折有可能丢掉。”
她一听,马上说:“严老师,这……这怎么办好, 你可要跟我保住啊,不能让它们丢掉呀。”
实际上,他们的存款不多。可是,气功讲“有得有失”,要解决一些问题,就得有些损失。我谈过 气功八十字,其中就有,“生死爱语舍”。厚厚一叠的气功书籍,从头到尾都讲这个“舍”字。要想得到功夫,要舍;要想病一下子好,要舍。要舍才能得。其中有奥妙,这个奥妙一下子讲不完。
我见她不愿“舍”,只好换一个方法。我说,“你回家打一盆水,悄悄地放在你家不容易看见的地方, 晚上要烧蚊香,改善你家里的空气。”实际上,用水,有特殊奥妙;烧蚊香,并非改善空气。我这里没有迷信的话,所以不存在迷信的东西。
因为她不愿失钱,所以有可能伤人。所以我说:“7天之内,你要照顾好你小孩和你妈妈。”
她说:“这个没关系,能照顾好。”
看她表这个态:她不愿丢钱,小孩和妈妈却没关系。这不招麻烦才怪哩!
我告诉她:“你明天不要说这件事,也不要去找。后天早上8时以后,人家上班了你就起床,起床后拉开床边的抽屉或书柜里的抽屉,支票会在那里。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,在第四天早上,你就要早于任何人上班,拉开办公室的抽屉,支票会在那里。 如果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,就只好采取第二种办法,就要毁掉支票。这事你就不要管了,这是我的事了。”
怎样毁?就是用水、用火毁掉它。毁的方式也多,如小偷洗衣服时会把装在衣袋里的空白支票洗掉,或者过河时掉在水中,空白支票被水冲掉或泡烂,或者抽烟时无意地把空白支票烧掉了。总之要用火、水。刚才我叫她打盆水放好,要烧蚊香,是有原因的,就是为了取信号。
我接着说:“上述的办法毁不掉,就只好通过其它方式使支票作废。”作废就不是毁的问题了,而是纠正一些人的思维的问题。
“第三个办法是只好教育小偷。”因为我们的原则是不整人,包括小偷也不整。所谓教育,就是叫他吃点苦头。如叫他去买东西,一拿支票出来就暴露,等等。
当然,最好是前两个办法。
第三天早上,她爱人上班前,把玻璃镜打烂了。她不起床,而为玻璃镜的事对爱人发了一顿脾气。爱人走后她又抱头大睡,8点钟过后还不起床,这样便失去了第一次机会。
说起来,这个同志连玻璃镜都不愿“舍”,怎么会“得”呢?到了时间,又不起床,她在想:反正有人给解决问题,起不起床没关系。机会就是这样错过的。
这天,她一直睡到中午12时,她姐姐回家叫醒她去吃火锅才起床,一吃吃到下午3、4点钟才回。
这时有客人来了,她忙于招呼客人,没有关照小孩,小孩站在桌子上一下摔下来,完了,摔成颅顶骨折。这不是一般的病,颅内出血是要死人的。 她马上抱小孩到医院照了片。我曾告诉她要保护好小孩,她就是心不诚,不配合,结果出事了。
当天晚上半夜三更,她又来找我,刚好我不在家。第二天早上,她找到我,一定要我给孩子治疗。这又麻烦了,在第四天早上又忘了打开办公桌的抽屉,错过了第二次机会。
我对她说,到医院去我不给治疗,因为医院人多干扰大,我的能量有限。于是,她通过熟人把小孩 捂着捂着抱了出来。
小孩在医院时头肿得很,摸不得,医院一直在观察,而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,我看了她小孩的脑袋后,就让小孩睡觉。睡了一个多小时,醒来后到处跑没事了。过后,我给小孩戴上我看病用的白帽子,说:“戴帽子一周,任何人任何时候,都不能取下,睡觉时也要用手拉着,一周后把帽子摘掉。”
这孩子平常不戴帽,结果戴了一周,正常了。可小孩的病刚好,她的妈妈,就是孩子的婆婆病倒了,要去住院。一年后我回去,听说她的妈妈还没有病愈。
支票的问题是7天内解决了。在第6天,突然到处登报,电台也发消息,说她单位的公章作废,旧公章盖的任何支票都作废。这问题就解决了。这当然是巧合,不能说是我给解决的。
我讲这件事,是想说明,有些事,从气功看,有点奥妙。有时候,就是要“舍”去一部分东西。所以气功老讲“舍”字,这个“舍”字,也是功德的范畴。
近年来,我给病人看病,不大喜欢给病人说病。以前看病,是经常说病的。
现在给人看病,也不愿意为人透视,遥诊。因为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曾派出由宣传部长、卫生局长带队的调查组作过调查,证实了我具有透视、遥诊等功能。我不需担心别人扣我“搞封建迷信”的帽子,也不怕别人扣我“弄虚作假”的帽子,更不需为反驳别人的指责而反复使用这些功能。功夫要会而不用、少用、慎用,才会上长。用多了, 就不好了。
况且,透视、遥诊方法经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因为用这些方法查的是病人以前患过的病,这些病未彻底好,被查出来了,有些人却矢口否认它。还可能查出将来才会明显表现的病症,有些人不信,反而说我胡说八道。所以带来麻烦不好。有些病症本来就不应该对病人讲,讲出来反而使病人背上思想包袱,以致影响疗效。当然,还有很多原因。这里说一个例子。
有一年,我回到老家,遇到一个干部。他搞过公安和人事工作,后来又转干别的工作。
我回到家后,几十个人找我看病,大家都说我诊断准确。给这个干部看病时,他也说我诊断准确。
为他看完病后,他请我为他两个小孩遥诊。他说了小孩的名字,但没有说性别。因为看病的人多,所以我边遥诊边带功开处方。他看了我给他两个孩子开的处方后,便翘起大拇指说:“我刚才没有说孩子的性别,你全写对了。”他两个女孩子的名字都是男孩的名字,他故意考考我。另外,他两个孩子的病我都说对了,其中一个孩子的第几条肋骨断了, 我都说对了。
接着,他又要我给他爱人遥诊。他的妻子当时在一千多里外的地方。我说了他妻子的病症,他先是认了,后来又给我出难题,要我看看他爱人以前患过什么病。
在我说他爱人做过阑尾切割手术时,他故意自言自语说:“哦,我以后告诉她要注意保护阑尾了,不要让阑尾做手术了。”我一听,他的话不是在否认他爱人做过切除手术吗?
我再次发功给她查,仍认定她做过阑尾手术,而且是十多年前做的。我跟他说了,他又重复刚才说的话。
我再查,证实我没有搞错,他硬是不承认。最后,他说不是阑尾做过手术,而是胆囊和胃做过手术。
我又查了她的胆囊和胃,否定了这两个部位做过手术。我说如果胆囊和胃要做手术,那可能是35年以后的事,那时可能患有胆结石等病。他马上不表态。
到了晚上,他对我妹夫说:“你的大舅可真有名堂,我爱人未结婚就割了阑尾,他给看出来了。下午几十人在场,我不好承认。”这证明我没诊错。
到了晚上,他又来找麻烦。他对我说:“你真有本事,你再帮我查查我在精神病院的岳父,看他现在病情是否好些了。”
我当时很不高兴,因为他在下午找了我的麻烦。不是为了面子,但几十人在场,这里可有个真实与否的问题!我对他说:“我不跟你查了,而且这个信号没有。”
后来他又告诉我妹夫,说他的岳父早就去世了。他出这个难题,是想捉弄我。
遇到这种专找麻烦的人,心情很是不舒畅。搞气功的人,吃苦没关系,但就怕受气,就怕别人找麻烦。被人搞了名堂以后,并非功夫用不出来,而是不愿用了。按功夫的进展来看,会而不用还可以上升,所以我现在不大愿为人查病。
1986年5月15日晚上,我到北京万寿路一个老干部家。他有个亲戚姓李,在北京某公司当经理。李经理要我给他看病,还要说他的病症。本不想说但没法。有些领导干部,你不说他不信,只好硬着头皮说了,而且说准了,他相信了。
接着,他又要我给他爱人看病。他爱人在40公里远。我对他说:“你爱人月经第5天……”
他一听就跳了起来,问:“你是不是认识我爱人,这些事她一般不会向人讲的呀!”
我说:“我从未见过你爱人,不认识。你爱人11 日来月经,今天是15日,当然是第5天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,还剩一点了,明天就干净了。”
他说:“你说得对,她的经期一般是4至5天。” 我说:“你爱人经期头痛特别厉害,平常也痛。” 他承认了。
我又说:“你爱人子宫里有些小毛病,但不好说,说了不好治疗。”
他非要我说,还说治不好没关系。
我说:“你爱人好象是有子宫瘤。”
他问:“是一个还是两个?”
我说:“是两个。”说完,我在纸上把子宫瘤的形状画了出来,并写出它的症状。
他看了,说我讲对了百分之九十九,还有百分之一没有说出来。
谈话之间,李经理拿出一份《人才交流表》让我填。他手中有点权,希望我能调到北京来。
我说,现在还不行,现在到处走一走,做点典型病例实验,为气功“正名”。如果气功“名正言顺”, 就会有更多的气功高手出来大胆地用气功为更多的人服务。我还说,我有单位,重庆是四川最早出特异功能者的地方,重庆对我也不错,所以还没有考虑离开重庆。
过了三天,李经理和妻子一起来找我,他对我说,15日晚我遥诊的结论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。原来在16日,他爱人去医院照片,发现子宫确是两个瘤。她说,一周前曾照片,那时从照片上看子宫只有一个瘤。她对我五体投地,说可能一周前的照片搞错了。
我说,不一定是照错。因为一个瘤子变成两个是有可熊的。